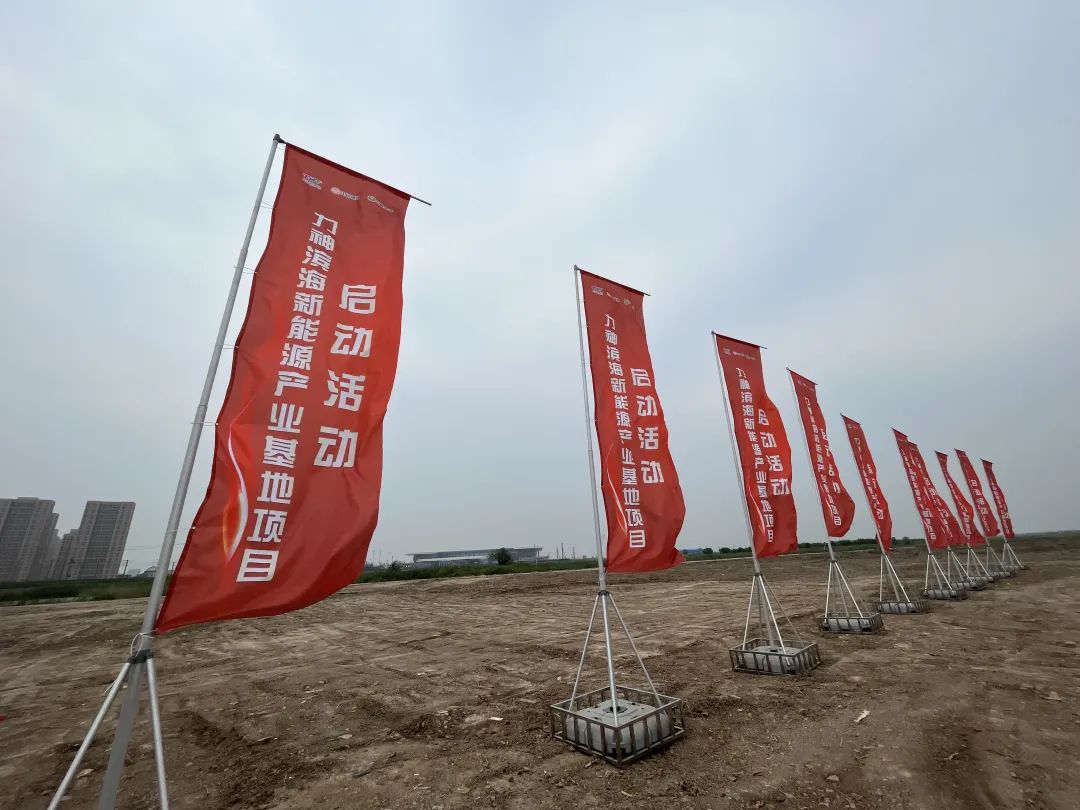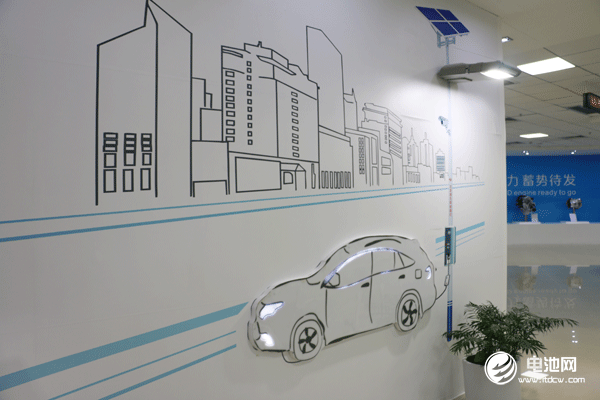編前:孫逢春,1958年生,湖南臨澧縣人。他職業(yè)生涯的40年,也是我國新能源汽車從起步到繁榮的40年。
自上世紀80年代了解到電動汽車是汽車未來發(fā)展方向開始,孫逢春幾十年堅守在這個領(lǐng)域,長期致力于新能源汽車整車集成與驅(qū)動理論研究、關(guān)鍵技術(shù)開發(fā)和工程應(yīng)用工作,提出并創(chuàng)建了中國電動車輛、充/換電站系統(tǒng)、車聯(lián)網(wǎng)等系統(tǒng)工程技術(shù)體系。
孫逢春一路帶領(lǐng)團隊攻堅克難,碩果累累,歷任國家新能源汽車專家組組長、北京市首席專家等,現(xiàn)為北京理工大學(xué)電動車輛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,獲評中國工程院院士。他帶領(lǐng)團隊完成了國家多個重要項目,榮獲國家技術(shù)發(fā)明二等獎2項、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1項,何梁何利獎1項及省部級獎多項。
從一片虛無到如今的生機勃勃,我國新能源汽車產(chǎn)業(yè)今非昔比。但孫逢春依舊做著他認為該做的事情,巖竹般寧靜挺立、柔韌如初。鄭燮《石竹》中“千磨萬擊還堅韌,任爾東西南北風”,就像在說他,堅守在新能源汽車領(lǐng)域,不管業(yè)界如何風云變幻。
我搞了近40年汽車,主要是新能源汽車。
我出生在湖南臨澧縣的一個偏遠山區(qū)。1966年上小學(xué),到高中畢業(yè),總共上了8年學(xué),16歲回鄉(xiāng)下干農(nóng)活兒,修過拖拉機和抽水機、當過民辦教師、做過磚瓦工等很多事情。后來研究電動汽車真得益于早年修理拖拉機鍛煉出的動手實踐能力。
1977年國家恢復(fù)高考后,我考上湖南大學(xué)應(yīng)用力學(xué)專業(yè),1978年入學(xué)。后來考研究生時回到老本行去搞拖拉機——北京理工大學(xué)車輛工程專業(yè),那時候叫汽車拖拉機專業(yè)。從理科轉(zhuǎn)入工科專業(yè),覺得數(shù)學(xué)考試太簡單,我花了30分鐘就答完了。學(xué)習車輛工程時主要方向是振動與噪聲,1987年去德國讀博士學(xué)位,選擇了輪胎動力學(xué)方向,跟當時吉林工業(yè)大學(xué)郭孔輝院士做的領(lǐng)域一樣。
■出國留學(xué)結(jié)緣電動汽車
我們這一代五幾年出生的人,留學(xué)是希望回國做點事情。當時在德國做博士論文時,我跟教授說,希望去德國三大汽車公司實習,多了解國外汽車公司。經(jīng)教授介紹,我在三家公司各實習了一個月。在這些公司里,有兩個地方是絕對不讓我去的,一是設(shè)計新產(chǎn)品的造型車間;另一個是新概念車間,研究未來技術(shù)和車型的地方。
盡管那時候中國已經(jīng)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大門,桑塔納轎車也在中國投產(chǎn),但當時中外汽車工業(yè)差距之大,讓我們這些留學(xué)生都有點抬不起頭。讀完博士后,德國大眾汽車公司想要留我,要么在德國工作,他們需要中德交流的人才;要么回中國籌建大眾的北京辦事處,讓我做籌建辦主任。我婉拒了大眾汽車的邀請,因為出國留學(xué)是想為中國汽車業(yè)做點事情。
在讀博士期間,我了解到電動汽車是未來發(fā)展方向之一,但并不了解詳情。由于跟教授做了很多項目,例如他的兩名助教做了5年沒有做出來的項目,我半年多就做出來了。教授也因此對我非常好。在回國前,我跟教授說想復(fù)印些資料帶回去,他就把復(fù)印室鑰匙給我,讓我隨便用。就這樣,我在圖書館找了很多電動汽車相關(guān)資料,復(fù)印下來,裝了一小集裝箱。當時就有預(yù)感電動車一定是未來的發(fā)展方向,想好好研究。
這是我跟電動汽車第一次結(jié)緣。
■“我們造出了‘遠望號’”
真正接觸電動汽車是在1992年。
我回國后在北京理工大學(xué)工作。當時國家的“八五”計劃已經(jīng)定了,也意味著我沒有項目可做。后來我申請了一個輪胎動力學(xué)自然基金項目,當時郭孔輝院士很支持,屬于青年基金項目,資金5萬元,當時還是一筆不小的數(shù)目。后來教育部還給了我3萬元優(yōu)秀回國人員基金做動力學(xué)研究。用了一年時間,項目順利完成。
1992年,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聯(lián)合開發(fā),把軍用電驅(qū)動技術(shù)轉(zhuǎn)為民用大客車技術(shù),中方當時是國防科工委牽頭支持,美方是國防部主導(dǎo)。當時在國內(nèi)找了很多院校和企業(yè)參與,比如國防科技大學(xué)、北京理工大學(xué)、西北工業(yè)大學(xué)、勝利客車廠、長安汽車等。項目調(diào)研時,北理工去了一位機械學(xué)院副院長。當時也沒人知道我懂電動汽車。后來項目需要一位外語好、懂業(yè)務(wù)的技術(shù)翻譯,那位副院長就找到了我。
項目談判歷時兩年,在第一次談判結(jié)束回來的路上,原國防科工委將軍沈榮駿對我說:“小孫,中方合作委員會的技術(shù)負責人就是你了。”1994年,就這么歪打正著,我36歲當了這個軍轉(zhuǎn)民電動客車的總工程師。
當時美方提供動力系統(tǒng),電機控制器、電池等,中方負責開發(fā)電動汽車車身和底盤。那時候我就想著電動汽車一定要正向開發(fā),我們應(yīng)該是國內(nèi)最早正向開發(fā)電動汽車的。
1995年,我們造出了中國第一輛純電動大客車“遠望號”。電動客車做得漂亮,項目很成功。
■“沒有核心技術(shù)給我沉重一擊”
電動客車項目做完之后,兩國政府提供的項目經(jīng)費用完了。當時是1996年,香港的中華電力公司想買這款電動客車,打了200萬港幣的定金。我們打算先做兩輛車,然后再批量生產(chǎn)。當時說得好好的,美國的西屋公司、格魯門公司(生產(chǎn)戰(zhàn)斗機)和休斯公司提供動力系統(tǒng)、電機控制器、變速器再加上充電機,一套價格是4萬美元。結(jié)果他們突然漲價到每套10萬美元。光是動力系統(tǒng)就已經(jīng)達到這個價格,入不敷出根本沒法做,只得把香港公司的定金退回去。
這算是對我打擊最大的一件事,切實感受到什么叫沒有核心技術(shù)。項目結(jié)束,意味著沒事做了。那時候感覺非常糟糕。
在1992年加入中美電動車項目之前,我已是北京理工大學(xué)振動與噪聲實驗室主任,當時這個實驗室是全校科研和經(jīng)濟效益最好的實驗室,因為全國都在搞汽車、摩托車的國產(chǎn)化。我同時還是汽車、摩托車減振器檢測中心主任。
但是,我從1994年正式進入電動車項目后就辭職了。我認為找到了正式項目,實驗室主任不當了。
那是“凈身出戶”。我跟自動控制學(xué)院一位老師帶著兩個學(xué)生,從學(xué)校借了一間廁所旁邊的儲物間做辦公室。曾去美國考察的那位副院長那時退休了,我邀請他跟我們一起研究電動車。當時什么也沒有,這個儲物間靠近廁所那面墻上全是水。買了四套桌椅、一臺計算機和一臺打印機,我們就是這樣開始的。
我?guī)ьI(lǐng)團隊做完中美電動客車項目之后,1996年遭遇美國公司出爾反爾的打擊。我們決定自己研發(fā)電機和控制器。經(jīng)歷了一年多的時間,我們做出來了。1997年,北京市正式立項,這是我國第一套完全自主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的電機電控系統(tǒng)、自動變速傳動系統(tǒng),而且原理上比國外要先進,能效比也比國外高。后來還獲得國家科技發(fā)明二等獎。
■在奧運會、世博會示范運營
之后我國開始申辦奧運會,1998年到2000年期間,我是北京市申奧交通領(lǐng)域的技術(shù)成員之一。國外評論北京空氣污染嚴重,在1999年申奧承諾里面就有一項:如果申奧成功,要在奧運中心區(qū)實現(xiàn)公交系統(tǒng)零排放。奧運申辦成功之后,新能源汽車就作為科技奧運的12個重點專項之一,我自然而然地成為此項目的首席專家。
我清楚記得,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主席在考察時對我說:“車不能出問題,因為24小時在運行。”為了奧運項目,我們做了很多技術(shù)攻關(guān)。要實現(xiàn)電動汽車在兩個多月內(nèi)24小時不間斷地運行,挑戰(zhàn)是很大的,而且技術(shù)人員進不去“鳥巢”那些場地,只能在場館外監(jiān)控。
2003年,當我知道技術(shù)人員進不去時,就搞了遠程監(jiān)控,在北京市道路上做電動汽車的可靠性運行。這就是今天我們所做的車聯(lián)網(wǎng)的前身。15年前受條件制約,也讓我們很早就開始研究車聯(lián)網(wǎng)。
研發(fā)團隊克服了很多困難,開發(fā)出完全自主知識產(chǎn)權(quán)的電動汽車,并在奧運期間率先實現(xiàn)規(guī)模化運營,取得巨大成功,當時也非常轟動。時任科技部部長萬鋼讓我?guī)ьI(lǐng)團隊去上海,幫助準備世博會項目。就這樣,后面陸續(xù)完成了世博會、亞運會等電動車項目。

 電池網(wǎng)微信
電池網(wǎng)微信